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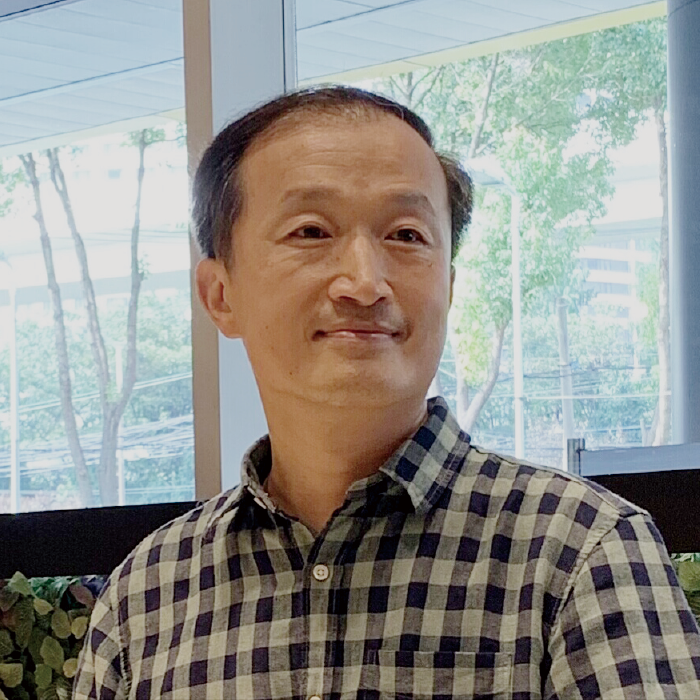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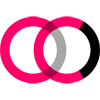














上海的髒空氣
我從來不曾吸過一口上海乾淨的空氣。整個上海的人都不曾。而我們都不知道。就像所有人都不知道,髒空氣裡其實藏著.....
不知為何,人們在和某種壞事初次相遇時,第一反應經常是以玩笑的心態面對,彷彿將事情輕鬆帶過,也就能輕易避開嚴重的後果。2013年底,突如其來的霧霾讓整個上海蒙上一層灰黃色,清晨的地鐵裡,上班族嬉笑地抱怨外面空氣就和擁擠的車廂裡同樣刺鼻,街角咖啡廳裡,解下口罩大口吸氣的客人,高聲分享著微博上與霧霾有關的新笑話和打油詩,這種對環境的調侃,來自無知也來自恐懼。

儘管刺鼻的空氣讓人們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但鮮少人會願意費心了解汙染物中的化學元素各會帶來什麼實質性的傷害,或是哪一種型號的口罩才能真正阻止pm2.5被吸入肺中。手機測量空氣指數的app剛剛下載好,汙染數值隨即「爆表」失去參考價值,空氣淨化器和口罩在數天之內被瘋狂搶購至斷貨。搶購,一向和天災人禍畫上等號。
霧究竟從何而來?城市不是沒有給過預兆:夜半在馬路上飛馳的砂石車,一面猛按喇叭一面捲起漫天塵土;黄浦江面扁平的運煤船,酷似一條條鼻涕蟲日夜緩慢行進;高架入口為了搶進車道的車群,在油門與煞車間不斷分散又聚攏,還有每次飛機降落上海前道別藍天的瞬間,就像是穿進了一個罩滿灰塵的水晶玻璃球內......種種暗示都曾晃過眼前卻又即刻被記憶丟失。只有在爆表此時,這些景象全部回歸,連成一條長條全景圖,人們霎時明白漫天灰塵並非一夕之間悄然而至,汙染的始作俑者遍佈各處,仔細回想起好像從來就沒怎麼呼吸過清新的空氣。
是不是任何城市發展接近極限的那一刻,一段難堪的蒙塵歷史就會變成它的背後靈?工業革命把英國從世界邊緣帶到世界中心,但倫敦自此展開百年霧霾,1952年底,一場毒霧終導致上萬人死亡。一度以煤火和高大煙囪自豪的大不列顛,才下決心改善空氣。同樣,另一座大城洛杉磯也從1943年第一次受霧霾肆虐,從此霧霾相伴的日子越來越頻繁,從一步步揪出罪魁禍首到制定法案逐漸讓環境和緩,耗費了數十年。
倫敦、洛杉磯乃至中國的京、滬兩大城,城市居民共性大概是一旦離大自然越遠就越大意對待世界。前兩座國外大城耗費數十年努力根除汙染帶了的影響,而現在中國才剛剛收到警訊,姍姍翻閱著對抗塵埃的歷史,準備找出借鑒之道。儘管有時代背景的差異不能完全相提並論,但這多也少意味著全速前進中的大國,也許必須用上未來數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反覆吸入教訓,才會甘心踏實面對這場嶄新的戰役。
幾個日子裡,掩面行走在迷濛城市確實打開了新的想像,也許這座城市有天真淪為科幻電影裡的廢城,在未來世界,人類最終只能向空中遷移,將地面完完全全留給塵土......然而,對於昨天而言,今天不就已是未來世界,但我們卻在每一個昨天理所當然又事不關己地大口呼吸。
這一次霧來之前,每當說起北京嚴重的空氣污染時,上海居民話語中總帶著與我何干的慶幸,甚至還帶著那麼一點點自豪的訕笑,但在上海霧霾最嚴重的那天,北京的居民推開窗卻發現空氣難得清新。一夜之間隨著霧起霧落,雙城關係巧妙地暫時反轉了。霧還會繼續在這個國度輪番駐留,人卻無法因為環境隨心變換駐紮之地,這是殘酷的生存法則,哪裡有污濁空氣,哪裡似乎就機會遍地。■
英語聯想:查理.狄更斯,《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本文刊載於英語島English Island 2014年2月號
訂閱雜誌
| 加入Line好友 |  |
 -- 作者:馬諦斯
-- 作者:馬諦斯數位編輯,在上海生活、工作、六年,攝影機是我的眼睛。人人都說上海這城市是世界的發電廠,而我總在城市的噪音裡聽到文化微弱的呼吸聲的那一剎那,按下相機快門。

 擔心生理健康,心理卻出問題?
擔心生理健康,心理卻出問題?


